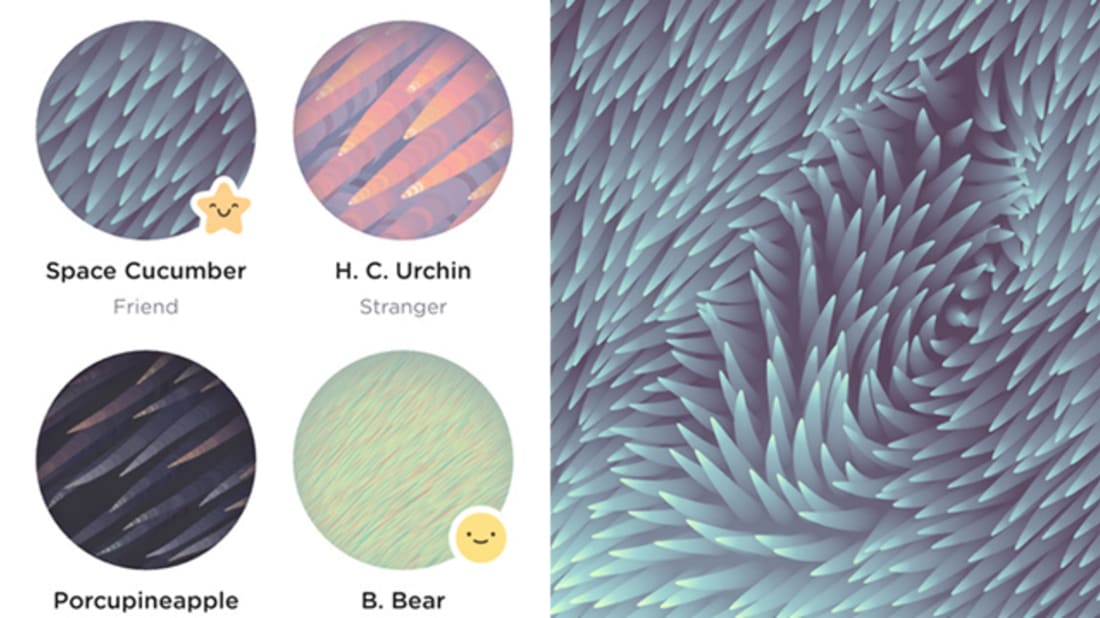1932年,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幼子被绑架并被发现死亡后,行凶者布鲁诺·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n)被绳之以法,随后就有了摄像机。在豪普特曼的审判和最终定罪过程中,如此多的摄影师照亮了法庭,以至于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成功地游说禁止摄影师参与诉讼,原因是他们会分心。大约30年后,在对杀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凶手杰克·鲁比的审判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聘请了插画家霍华德·布罗迪来捕捉Ruby的表情。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大部分都是用木炭和水彩画出来的。法庭上的素描艺术家们会去到摄像机无法到达的地方,记录下诸如查尔斯·曼森、伯尼·麦道夫和迈克尔·杰克逊这样备受瞩目的司法案件中经常出现的紧张气氛。在紧迫的期限内,这些艺术家用他们的技巧来传达法庭上的情绪。
但光有才华还不够。速度是至关重要的,找到合适的场景来概括一整天或审判也是如此。“这很难做到,”加州法庭插图画家莫娜·谢弗·爱德华兹说。“这不是漫画,不是漫画,也不是肖像。它捕捉了一个瞬间。”
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作品,Mental Floss采访了目前工作的三位最著名的艺术家。以下是他们对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总结。
1. 他们必须绕过障碍。

想象一下,你坐下来为一个朋友画素描,发现有人在你的视野中直接放置了一个柱子、屏幕或身体。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不能捕捉到这个人的肖像,你就得不到报酬。这是法庭素描师最常遇到的问题,他们经常要绕过障碍才能看到他们的主题——通常是被告、律师或法官。“你通常得等着有人俯身过来,”在CNBC和美联社工作的纽约艺术家伊丽莎白·威廉姆斯(Elizabeth Williams)说。(大多数艺术家受雇于大型新闻媒体)“幸运的是,人不是盆栽植物,他们确实会搬家。”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威廉姆斯会自己在法庭里四处走动,试图获得一个更好的有利位置。在答辩和判决期间——取决于法官——她可能被允许与其他记者坐在陪审席上。
如果视觉障碍仍然是个问题,一些艺术家可能会求助于家庭成员。维姬•艾伦•贝林格(Vicki Ellen Behringer)在加州为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福克斯(Fox)在内的客户工作,她说,当她见不到被告的儿子时,她曾经用他的父亲作为参考。“我研究过他儿子的脸,他的父亲让我想起了他的长相,”她说。“他们看起来太像了。”
2. 年轻人比较难画。

对贝林格来说,拥有丰富特征的脸是一份礼物。她说:“我喜欢眼镜,我喜欢胡子,很多皱纹,任何能显示个性的东西。”“最困难的事情是和一个年轻英俊的人约会。她们脸上没有皱纹。”贝林格引用了“大学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上图)和他的律师坐在一起的画像。卡钦斯基饱经风沙的样子很容易渲染,但他的律师——年轻且线条相对松散——却很难捕捉到。
3.早晨对他们来说比较好。

素描艺术家在高压锅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经常被新闻机构在一天或更短的时间内传唤到法庭,并且需要快速地完成他们的绘画。如果审判的关键时刻发生在下午晚些时候,艺术家们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作品的上色,然后扫描并将其发送给与作品签约的新闻媒体。威廉姆斯说,在晚间新闻节目中,“要迅速扭转局面的压力很大”。如果早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改进工作。“那时候没人会盯着你。”
4. 他们因为渲染名人形象而受到指责。

因为人们对名人都很熟悉,所以看到一幅没有排列整齐的宫廷画像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爱德华兹认为,这是因为名人不一定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因为让格温妮丝·帕特洛看起来不好看而受到嘲笑,”她说。她指的是格温妮丝·帕特洛在2016年出庭指证丹特·迈克尔·索乌(Dante Michael Soiu)——一名被控跟踪她的男子——时的表现。(他被判无罪)“她没有化妆,穿着米色的高领毛衣,鼻子哭红了。”帕特洛的粉丝批评爱德华兹的形象不讨人喜欢。
5. 他们有时会在纸上重新安排法庭。

据威廉姆斯说,一些新闻媒体对素描艺术家如何诠释法庭场景有严格的规定。例如,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就不允许艺术家在一个人接近另一个人的情况下捣乱。如果被告离他或她的律师只有四英尺远,威廉姆斯不能让他们的肩膀接触。但其他渠道允许艺术创作。贝林格说:“有时候,你不可能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也不可能做到准确,所以你只能把它们挤在一起。”“有时候,你希望被告像法官一样,或者把辩方和控方的桌子移得更近一些。”
6. 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卖给律师。

就像大型狩猎者一样,律师也喜欢战利品。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的律师会联系威廉姆斯,要求购买她绘制的一幅素描。“我已经把我的作品卖给了很多律师,”她说。“一般来说,他们只有赢了才想要。”贝林格说,一些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会特别要求她到法庭来描述他们。“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向父母证明你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
国会图书馆甚至收藏了96张来自著名审判的法庭绘画,其中包括威廉姆斯的插图。它们是用洛杉矶著名律师托马斯·v·吉拉迪(Thomas V. Girardi)的资金购买的。吉拉迪以参与涉及《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的加州环境污染案而闻名。
7. 有时实验对象会要求改造。

有时,辩护律师或其他法学家会联系爱德华兹,问她的工作是否可以更讨人喜欢一些。“男人们会来找我,要求我给他们多留点头发,或者让他们看起来更瘦或更漂亮,”她说。“从来没有女人要求我减肥或做其他事情。它总是男人。”
8. 圆点图案和条形图案都是坏消息。

素描师需要花时间捕捉和提炼情绪和情绪。如果被告戴着指纹,这可能会让人恼火。“黑色衣服上的白色圆点在水彩画中很难画出来,”贝林格说。“条纹。你不想浪费精力让衣服变得准确。我宁愿把时间花在脸上。这可能会令人沮丧。”贝林格的另一个忌讳:酒吧。在加州,一些被告在法庭上被传讯在一个小牢房里,让艺术家们在栏杆后面试着画他们。贝林格描绘了金州杀手约瑟夫·詹姆斯·迪安杰罗在他的迷你监狱里的样子(上图),仔细地画出了将他与文明社会隔开的每一个酒吧。“这非常耗时。”
9. 他们有时提前练习。

当艺术家们预订审判时,他们知道他们可能只有一毫秒的时间去看被告的脸,然后他或她要么被带出法庭,要么坐到视线之外的座位上。为了更好看,艺术家们有时会在审判前在家里用现有的照片作为参考来做草稿。“偶尔我会和名人一起练习,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贝林格说。“即使他们不是名人,在照片中寻找某些特征也会有帮助,因为你可能在法庭上看不到。”
10. 他们的研究对象很少合作。

与普通的画像主体不同,被告和其他法庭人物通常没有很大的动机与素描师合作。他们会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表情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很难确定。在报道2018年8月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见上图)和他的逃税联邦听证会时,威廉姆斯被他弹性的脸吓了一跳。她说:“如果有人只是坐在那里,就好像在说,‘好,明白了。’”但在他的演讲过程中,他过度紧张,情绪从恐惧到抑郁,甚至哭了起来。当人们做出很多表情时,要让表情看起来像他们是很有挑战性的。”她画了17个科恩头像,最后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
其他时候,被告可能冷酷无情。在记录2016年杀死10至25人的“冷酷的沉睡者”小朗尼·大卫·富兰克林(Lonnie David Franklin Jr.)一案时,爱德华兹惊讶地发现,他似乎对审判无动于衷。“我一直盯着这个人,等着他有所反应,”她说。“他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2013年,臭名昭著的波士顿黑帮成员詹姆斯·“怀特”·巴尔杰(James“Whitey”Bulger)在逃亡多年后终于被绳之以法。巴尔杰直直地看着她,在试图捂住脸之前摇了摇手指说“不”。
11. 他们在艺术上与法官建立联系。

大多数艺术家与法官关系良好,法官欣赏他们记录重要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工作。有时,法官甚至会决定谈论本行。爱德华兹说:“我让评委买了我的画,带我去他们的办公室,向我展示他们自己的作品或他们的艺术收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品味和眼光。”
12. 被告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貌。

有些试验可能意味着日复一日地画同样的面孔。其他时候,被告将经历一些相当激进的身体转变,让素描艺术家保持警觉。贝林格说:“巴里•邦兹(Barry Bonds)从(2007年,因作伪证)被起诉的那天起,到审判结束的那天,他瘦了很多。”“在斯托克顿还有一场审判,被告的体重增加了很多。人们说是因为监狱食物里的碳水化合物。”
最引人注目的外表变化要数已故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上图,与杰•雷诺在一起)。2005年,杰克逊因涉嫌猥亵儿童而受审,在受审期间,他经常被素描。(陪审团判他无罪)”每天,他都穿完全不同的衣服,不同的臂章,从周一到周五他的头发也会变。有一次,周一的时间更长。就像,你是怎么做到的?”
13. 他们尽量安静地画画。

当摄像机出现在法庭上时,每个人都知道。当爱德华兹在的时候,实验对象甚至可能不知道他们正在被渲染。艺术家随身携带一个9英寸× 12英寸的小垫子和一些工具。“被告从来不知道我在画他们,”她说。“如果你意识到有人在盯着你看,你可能会表现得不一样。我试着融入人群。”
14. oj·辛普森可能让他们继续经营。

1995年,辛普森被控杀害前妻妮可·布朗·辛普森和她的朋友罗恩·戈德曼,允许电视摄像机拍摄对辛普森的审判的决定似乎标志着法庭媒体报道的新政策的放松。“我想这就是素描的绝唱,”爱德华兹说。“结果这只是个玩笑。”法官们担心他们会像辛普森的首席法官兰斯·伊藤一样受到批评,因此回避了这种审查。“评委们意识到他们不想上镜。所以每次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它却还在继续。”
15. 他们的婚礼。

随着一些联邦法院对摄像机的存在越来越宽容,法院素描业务的性质在这些年发生了变化。(虽然联邦审判法庭通常不允许使用摄像头,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实验和试点项目允许使用摄像头;国家规则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艺术家仍然会找到工作,但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方式也是一个好主意。威廉姆斯会在周末法庭不开庭的时候为婚礼安排素描师的工作。“人们总是会结婚,但你不能总是指望‘矮子’会被捕,”她说。“你必须做其他事情。”威廉姆斯对待婚礼的方式与审判非常相似。“我会去见一个客户,回顾一下关键时刻。”这可能不是结案陈词,而是作为已婚夫妇的第一支舞。
最大的区别?“和这些快乐的、刚刚开始新生活的人在一起真好,而不是那些要进监狱的人。”
为您推荐:
- 这个小小的可穿戴磁盘存档了一万年的1000种语言 2022-03-11
- 来自美国各地的11个“精疲力竭”的习语 2022-03-11
- 什么语言最难学? 2022-03-11
- 与伟大的美国文字绘图仪的乐趣 2022-03-11